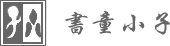|
《 散文 》 | |||
| « 诗歌 | 摄影 » | ||
|
《禦園十歲》
禦園十歲了。 十年之前的今天,29位來自北京的師傅正在匆忙中,為祥雲宮的外衣著上最後的紅妝。太冷了,零下5度,大紅襖被霜凍上了,滲出片片晶瑩的冰淩花。。。祥雲宮,古樂亭,石頭桌凳,還有石橋,伴著冷清的園路,凸赳赳,孤愣愣地站著,在被翻新的施瓦本黃土地上,在藍汪汪的天空下,紅樓閣紮著人眼鮮豔,一點都不知道害羞,被好奇的圍觀照相,上報紙,登雜誌。 禦園是美麗的。 春天裏,來自山東菏澤的富貴牡丹,被一片碩大潔白的妁藥伴陪著盛開,孩子气的我喜欢泼泼辣辣的植物,不爱搭理娇嫩羞涩的花朵。直到去年,那十几朵累弯了花枝的牡丹倒在园路,截住了散步的我。我撿起來,它們的美麗讓我流了眼淚!在這個世界上,嬌嫩短命的花朵才是最彻底的"唯美主义的生命代表: 看,我的君子兰,"。。。依在籍孤中風流,。。。偎在橘色中夢遊。。。"純粹的美不僅僅將人置身於一個陶醉裏,熱烈地讓人心跳,還引來了成對成雙的野鴨,下蛋孵小鴨,吵醒冬眠的大鯉魚,唤醒了春眠的懒虫。 盛夏之夜,姣月亮和白蓮花飲著同一彎清水,醉醺醺的親密低語,朦朦朧朧的曖昧, 擾得我心癢癢。。。我,最愛這恒久的幸福了! 我的幸福,是只歸家的小船,躺在溫柔的沙灘憨憨睡覺 我的幸福,是片金色的秋葉,掛在如絲的枝條自在逍遙 我的幸福,是這冬天的野火,在寒冷的狂風中奔騰呼嘯。。。 園子的大石頭們也來自中國,一共378個立方,滿六隻大集裝箱呢。姣月亮和白蓮花飲著同一彎清水,醉醺醺的親密低語,朦朦朧朧的曖昧,擾得咪咪心都癢癢,依偎它愛戀的石頭,撒嬌癩皮。咪咪愛的只有一塊,嘻,還挺專一的呢,這事只有我知道。 濃濃的色彩結結實實包圍著秋天的果實,在這個季節,樹葉最染我作品,攝影,還是攝影,貪婪地忘乎所以,我常常為忘記趕在落日時拍出霜槳紅了葉子尖的水仙花而懊悔。 冬天,園子依舊鬱鬱蒼蒼的綠著,竹子不經意就顯出了它們的高節和韌力,如雨後春筍直述他們那旺盛驚人的生命力那樣,冬天裏他很任性的訴說他的情懷:君子的,獨尊的,始終如一的,主人公責任感的,超越四季的抗旱禦寒能力。 園子是文化的。 祥雲宮建築總面積1000平米,九大開間,純木結構,它使用了489立方原木材,北京的師傅說,這樣九開間的純木結構古建大宮殿,在北京都40多年沒有見過了,是屬於皇家園林裏最高級開間了。(北京故宮太和殿是11開間)庭院和樓閣成了我藝術攝影的"模特"兒。我記下花草樹木的成長筆記,錄下了很多獨特的景致。它也夠神了,好像還沒有開始成長的時候,就被人們迫不及待的捧為"星"。在一夜之間就成了"明",進電影故事,上汽車行封面,還是健美健身旅遊社的長期夥伴。我呢,像伴隨他成長起來的一棵永遠長不大的小樹,很粗野皮實,沒大沒小的,喜歡和努曼釣魚,和院裏大大小小的聊天,偶爾,興致來了,喊兩嗓子,給好奇的宣傳中國園林藝術,安靜時,居然能畫幾行詩來。我想我應該是這個"大文化"裏的小"土八路",正如,在祥和的霓虹燈下,我是一個哨兵。很有光荣感,小兵张嘎。 園子不僅僅是文化的,更重要的,禦園還是生活的,踏踏實實的生活的。 施瓦本的居民特別愛這個中國園子。天天,人們帶著孩子,狗兒來院子散步,週五,週六,那剛剛在市政廳辦玩登記的新人,著著婚紗,在家人的簇擁下,來院子裏拍照。不知道何時起,花花公子們也看上了紅樓,"攝影師舉著這麼大個的攝像機,那女子的胸這麼飽滿,一絲不掛。。。"70多歲的努曼手把著大紅門,蹺腳抬腿學那紅塵女子的樣子,"上次一下子進來一幫,你看我記下了車牌號。。。肯定是給電視臺製作晚間廣告。入鄉隨俗吧,我想,生活需要必要的激勵。那天和克裏斯特屈指一算,弗萊堡的MARKTHALLE這個22個國籍人種的大家庭裏,不到十年添丁近三十,真可謂生意紅火,人丁興隆。可報紙上說,德國有四分之一的家庭無生育能力,義大利更糟糕,這樣下去,再過100年,只餘下一半人口,生活向何處去呢? 你看,禦園是世外桃源了。"小蘋果"在第三年上開花結果,從此不分大年小年,一路年年果實累累,那鮮紅鮮紅的小果子成串的掛在樹上,成了鳥兒冬天的食堂!多的時候三十五十的來,大大小小的,嘁嘁喳喳聊天吃飯,熱鬧得氛圍讓人心醉,好羡慕這個和睦的大家庭。 我的小湖,無名的靜湖,永不瞑目的小湖! 写御园,不能不写它。很多人問過我,中國的園林為什麼一定備湖呢?我就指著祥雲宮的頂,看,這是龍宮啊,兩大龍,四小龍,每條龍備了三隻河馬。巨龍佩六馬。。園子沒有水怎麼可以那!再說啦。。。我也不知道了,嘻嘻 我的小湖,無名的靜湖,永不瞑目的小湖! 永遠睜著它好奇迷人的眼睛 , 依舊忠實的看管照料湖畔上 , 千歲的柳,百日的物,十辰的雨,一分的蟲! 小湖至今無名。在有名的禦園裏,好像註定了她無名。其實她是鏡子,有誰還給家裏的鏡子起出第二個名字的?風兒,靜靜的躲在咪咪柔軟的細毛裏睡了的時候。。。小湖平靜的聆聽泉水嘩啦嘩啦唱歌:在水一方,在水一方! 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 我是那永不知足的不倦不瞑! 我是月月之物,隨山轉在地遊 我是日月之物,隨雲遠,走高飛。。。 古樂亭名副其實,古樸而敦厚。想當年,不懂事的我還曾設計改圖,嫌棄四角亭土氣呢。如今燕堂閑坐,靜觀月洞門上的 "松風"和"竹月" 磚雕,此實情此真景,恰好應了一首愈過千載的古詩: 天網疏難漏,世網密不通,我心久不動,一脫兩網中。 高竹漱清泉,長松迎清風。又雲:瀟灑松間月,清冷竹外風。 此時逢此景,正與此心同。這不正是古樂亭閑坐的老子賜給禦園的嗎?肯定是的。不信的,你來,園內每一個存在都會告訴:平安說的真而實。那詩就是為今日的景致準備的。 神覺開,安平泰,得希夷樂,無崇辱驚,攬萬端事,入一聲歌:此時逢此景,正與此心同! 咪咪七歲了。七七四十九,我們以後可以叫咪咪"老夫人"了!除了努曼,它比我們任何人,更熟悉園內的草木小蟲,知道兩家黃鸝何時在祥雲宮的牌匾後面作窩,耐心地仰臉盯著小黃鸝出窩散步。隨時出擊捉來一隻玩。兩隻老黃鸝緊追在咪咪身後,和咪咪講理要孩子。發了慈悲,還給它們罷啦,嘻嘻,咪咪還了人家。它過於善解人意的行為,竟惹得主人發大脾氣,揚言道,誰站在咪咪一邊,誰就是奸臣,替咪咪說話的就是"何坤"。我說咪咪,你是奸臣,我是何坤。嘻嘻,哥倆好。天氣這麼晴朗,俺倆照張合影!咪咪扭扭捏捏,來院子散步的狗趁機跑來,偎在我的身邊臥倒,擺出了照相的姿勢。咪咪氣得好幾天不搭理人,還把來家裏討它飯食的狗給搧了。。。 看!那傍守小湖的柳"成人"了!在這個深冬的季節,和那些英姿颯爽的青竹們一比,倒更像謝了頂發的老洋頭,垂著軟塌塌的金髮。 "情如落絮無高下,心似遊絲自往還。又恐幽禽知此意,故來枝上語綿蠻。"嘻嘻,我那不懷好意的狡詐眼神兒,惹得那老柳有點嗔怒:看什麼?你!別添亂啦,沒瞧見這幾隻不知趣的鳥兒在頭頂上嘁嚓了快一天,我煩著呢! 啊?在這個寧靜的,悠閒的,忙碌的,熱烈的世界,所有的存在都在一個陶醉中,好像都遺忘了一個事情,好像還不是他們思想的事情:十年之前,這裏,就是柳樹湖畔上,沒有紅房人家,沒有石橋溪水,沒有。。。現在有的那會兒什麼都沒有。對了,這是一片麥地。我們都從無而來!從一個意願,同源攜手而至。從簡至繁,從往至複,從無到有,從有到無。。。 百年之後呢?我肯定不在,那只吵鬧的鳥肯定不在,禦園在嗎,大柳樹會是什麼樣子呢?我也不知道。都逝去了嗎?我也不知道。 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 啊!我們真的沒有必要多事,多嘴多舌,"。。。此三者為不可致答詰問之物。故混合而為一是謂道之整體"。我們沒有遺忘什麼,我們也不必擔憂什麼,和和睦睦生活在這裏,瞬間不就是永恆嗎?是的,肯定是的! 對於我,禦園的成就展示了人文,化物的真實經歷。我知道,唯有一個永恆的存在者:那是至善的意志!最美好的希望,最完美的生命都源於他,萬物和世界都源於他!那是我们生命绵延不绝的慧根,万物和世界的根源之国:大自然,我們永恆的家園。 是的,肯定是。這麼自信?當然啦,因為我們都生活在這裏!和老子一起生活在這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