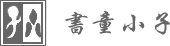|
《 散文 》 | |||
| « 诗歌 | 摄影 » | ||
|
《舜,帶我回故鄉童年》
舜,帶我回故鄉童年 。。。 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於帝。浚哲文明,溫恭允塞。玄德省聞,乃命以位。。。 正月上日,受終於文祖。 。。。歲二月,東巡守,至於岱宗,祡。 。。。海,岱惟青州:愚夷暨洛,濰淄其道。厥土白墳,海濱廣斥。厥田惟上下,厥賦中上。厥貢鹽悕,海物惟錯。岱畎絲, ,鉛,松,怪石。萊夷作牧。厥篚湹絲。浮于汶,達于齊。 在彌漫著墨香的《舜典》裏,我停下來:久違了!這裏是我的故鄉!這裏有我的童年。泰山汶萊,我熟悉親切的氣息! 用黍秸杆插成的風車在我的奔跑中裏轉動起來,那輕微的響聲,忽忽忽忽,帶出來了我的童年。。。 哥哥說,我出生在岱宗坊旁邊的小院子裏,泰安泰山腳下。在能夠清晰的記憶裏,我是"外甥狗",住姥爺家莱芜,萊蕪一中的大雜院裏有最美好的童年。 不知道究竟為什麼,除了現在中國日報擔任總編輯的朱英璜老師,再也沒有第二個教過我的老師的名字存儲在我記憶裏。可是,我卻能描繪出童年大院裏田校長家裏的擺設,文琴俊俏臉上永遠微笑的那只單酒窩,記住了院子裏每一個大人孩子的名字相貌,大院角落裏中藥房濃濃的蒿草香,還有自己踩著板凳,照鏡子量腰圍的模佯。後院的教導主任每次見我,就喊我,嗨,"喝西北風長大的"。。。 從一中大前門穿過光滑的青石板大街,跑100大步,經過三家住戶和一個菜園子,就是汶河。 美,永遠是故鄉水。親,永遠是汶河水。儘管,弗賴堡河裏的鵝卵石很近似汶河裏的,儘管我游了長江的三峽,生活濟南的黃河,最親最美的永遠是生養我的汶河。 汶河是沙河。沙灘寬敞無盡。汶河的水將汶河裏的沙打磨成我們的遊戲場。站在田校長家的合真,林會計家小三子的肩上,他們馱著我輪流在沙灘奔跑,叫啊笑啊,一起摔進沙堆,沙灘托著我們的歡樂。絕不會摔疼的,沙子特別輕軟,有彈性,顆粒均勻,不粗不細,我們無意中常常把它們帶回家。姥姥天天"掃炕"炕上淨是汶河沙,很疙睡覺的人。。。子玉說,汶河的沙有砂金,早先人們都在汶河裏淘金。 我們孩子們也玩貼金:我們光屁股趟一身水,就跑到暖洋洋的幹沙灘結結實實打個滾兒,坐一會兒,就各自相互囫落身上的沙。細細的沙金片緊緊抱著我們的身體,五顏六色閃閃發光,再停一會兒,我們就一點一點將吸在身上的細片片(沙金)使勁兒擼下來,收進一個小布袋子裏,帶回家。日複日,年複年。。。長了,家門口竟堆了好大一堆沙金,成了後來表弟東明開軍艦的"大海"。 我喝羊奶長大。隱隱約約記憶中,有自己和那只大白羊玩耍的影子。後來,西廂房讓給了一位新來的住戶,就沒有地方養它了,給了校外對街的"回回"奶奶。回回奶奶家院子很大而擁擠,有馬,騾子,牛,羊,狗,雞鴨鵝成群。。我常常擠在一直不下炕的奶奶身邊,端著磁缸子喝鮮奶。奶奶的床可大了,好幾個孩子一起在上面跳舞。。。 回回奶奶死了,他們將奶奶洗擦得乾乾淨淨,放在院子裏支好的木板上,一個大男人把奶奶身上所有的毛髮全都剃得一乾二淨。我跟著大男人們,擠在前面,仔細觀看。。。在做完了這一切之後,他們用一匹漂白的白布將奶奶完全裹起來,放進棺材。沒有人哭,很安靜。出來大門,外頭一片呼天喊地的哭聲,那些哭喊的人戴著白帽子,全身也包上了白布,我都認不出是誰來了!哭聲很刺耳,我跟著走到校一中大門口,轉彎回家了。後來子玉說我,你這個孩子給他們哭得嚇掉魂兒啦!半夜喊叫,連續整整個把月。。。 我不知道我曾喊叫過,可我記得,夜裏我最緊張的時候會出現一個我又害怕見卻還特別想看的奶白色的特別清楚的小東西。。。一直沒有問子玉,更沒有告訴任何人,這是我的童年最大秘密。這個秘密直到在老子的一本書裏打開了:它是誠神叽圖。 喜歡跟姥爺一起去酒廠打酒,一進廠大門,酒糟香味迎面而來!我使勁兒吸鼻子,真香,真香!姥爺指著那堆"黃沙"說,這是酒糟,可以喂豬。。。回家的路上,一過汶河大橋,姥爺停下車子,右轉進汶河沙灘,將車子靠在沙棗樹棵上,哼著曲兒,背起雙手,走進樹林深處。我就在車子旁邊樹棵下,和可愛的灰色沙蟲蟲玩。這種小蟲象汶河的沙子一樣乾淨俐落,跑得很快,一眨眼睛,就鑽入沙裏,我翻來覆去找他們。。。直到姥爺喊,走了,回家。我才跳上姥爺的車子,唱著歌快樂地回家。。。 姥爺的"洋車子"是綠色的,很時髦漂亮,常常招徠羡慕的眼神,今年春節我才知道,車子是父親送給姥爺的。姥爺很喜歡帶我的和表弟一起出門。東明坐在前面擋杆上,象我從前那樣,我坐在車後座上。每次一過高橋,弟弟就喊:別拐彎!別拐彎!姥爺哈哈笑著說,不拐彎,不拐彎,說著說著拐進幼稚園大門。。。子玉對我說,東明憨厚,不象你,犟! 舅舅來家啦!家裏像過節日。平日話語不多的姥爺和舅舅嘻嘻哈哈,滔滔不絕。我也學著大人叫舅舅"衍琴",搶著說話,仰著臉叫"衍琴,轉一圈",舅舅說,好,就在屋中間將我高高的舉起來,轉好幾圈!快樂的我跑到鄰居家學舌:老娘說,這是舊習,男兒起個女兒名好養活。我舅上大學被分配到女生宿舍,哈哈哈哈。。。 童年的夏天出奇的長!在汶河沙水裏一天可以當好幾天過,大人們都午睡,孩子們就爬樹粘那煩人的知了,熱了,下到汶河撈魚,累了,倒在烤人的沙灘上睡覺。一覺醒來,太陽還高傲著呢!扒開身邊的蘆葦根,有滋有味的嚼赤。來精神了,再給和真家采很多桑葉,我們一起在她家養了很多絲蠶,不幾天就要吐絲結繭啦。。。一中北門(後大門)馬路對過就是鋼山,黑天了,我們幾個結伴去鋼山鐵廠看電影。 夏天裏我的童年長過長江!好像整年都可以打赤腳,直到去濟南念大學之前,一直喜歡赤腳走路,很省鞋,鞋子只有不得以時才勉強套在腳上。。。 冬天的記憶極短。最喜歡一腳伸進比我的腳熱呼很多的棉鞋裏那個感覺。那是子玉帶給的。歷歷在目的是灶臺上乾巴巴的地瓜,子玉給我烤的"烤地瓜"。我至今最愛吃的食品。可能與不斷的想念,精確記憶關係密切。和地瓜很親很近,從來沒有厭倦過它,它的香味沁入心地很深很久。到了姨家後,上縣中學的路上,每次經過地瓜地,都拿腳踢出一塊,邊走邊吃。地瓜不熟的嫩生味象嚼生面,半熟的跟生茄子相似,成熟的地瓜甘甜,經驗告訴我那一壟的地瓜脆而不茛,那種地瓜咬也咬不動,好像啃南街回回奶奶家喂馬的生豆餅。 不論什麼地瓜,不論何時何地,都會令我想念子玉,小孩的眼淚從來不容許任何人看見。有人在場,忍不住淚我就掩飾地說,地瓜太靦,噎得。。。去年,和親如兄弟的卡爾聊天,卡爾無意中說出他最愛的人是他的外祖母,講了他和外祖母一起的生活。聽著聽著,我忍不住哇哇哭起來,第一次當著人說,我想子玉,我想子玉,我的姥姥。我從11歲就離開她,我想她。。。。前幾天,小子親兄誇獎我"勤力"。這倆字久違而親切!是迄今為止只有子玉用來誇獎我的原話。。。姥姥說我是強驢,只能順著毛摸,說我"勤力伯夥,掙點吃喝。" 也許,子玉將"勤力"傳給了我,並使我愛上了冬天,那熱呼呼的棉鞋,爐臺的香噴噴的地瓜,以及天還不亮就爬起來,能和子玉一起,分享冬日裏一份特別的清涼。 在獨立的日子裏,我漸漸知道了,子玉給我的竟是人生最基本的需求。此外,人不需要什麼了。唯有勤力,是自立的根本,有了它,人們的生活裏什麼都不會欠缺的。我如此想念她,實際上因為這是我必須依賴的存在的本根。。。 有一陣子,子玉執意,回佛家莊子老宅住。姥爺的佛家莊子離縣城一中好像十幾裏路。那是一個很大的四合院,空曠寬敞,乾淨俐落,只有一顆小石榴樹。西門過道是我六姥爺家果樹滿院的小院子。他的大黑豬養在我姥爺大院的大豬圈裏。那種短嘴巴圓臉龐漂亮的黑豬,我從此再也沒見過。去豬圈方便前,先叫六姥爺來幫我把住它。我怕它拱我!六姥爺家的小女兒,我的小姨笑話我,給我一根竹竿,說,它拱你,你就打它。。。 小姨比我只大一歲,可是個頭比我還小,長得真俊!俊得我都不敢多看,揪著人家的砕花棉襖,說棉襖好看。好像最美麗的東西是專門供人來想念的。 真想讓我的文字像她那樣俊俏,至少染上點她身上的暖氣,加上她那棉襖印花的清秀! 還是很想念故土泰山汶河的,想念姥爺念慈和姥姥子玉,是他們,留給我一個金色的永恆,恒久美好的記憶! 讓我用《木瓜》一樣的誠實(木瓜在老家也叫香瓜),傳達給生我養我的祖先和故鄉一個小小心願。。。 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匪報也,永以為好也。 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匪報也,永以為好也。 投我以木李,報之以瓊玖,匪報也,永以為好也。 |